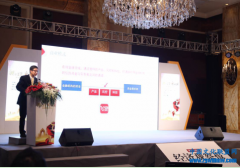李冬君
用观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之眼,瞭望早前一个世纪的中国宋朝,那里所呈现的基于人性塑造历史的景观,竟然与地中海的浪漫情调多有相似。当我们发现那里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给予自己所能创造辉煌历史的最佳褒奖时,便再也无法按捺穿越历史的兴奋,用“文艺复兴”的门票到宋朝去逡巡游览一番。
皇家画院的艺术家们
宋徽宗赵佶,半百人生54年,红袍着身25载,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留下一笔的惨淡只影,在公元12世纪初便转瞬即逝了。脱脱撰写《宋史》,写到《徽宗纪》时不由掷笔惋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此论几为后代评价宋徽宗的基调。宋徽宗在太平盛世做了太平皇帝,却沦为乱世囚徒,客死他乡,断送了王朝,断送了自己。上述为王朝史观者扼腕之共识。
的确,“独不能为君耳”,使一个伴随文艺复兴而即将迎来的近世国家,就这样在文艺复兴中毁失参半了。国土沦丧,百姓流离,作为一国之君,他难辞其咎。“诸事皆能”,恐怕连脱脱都能依然感受到赵佶的才华遗韵以及他为两宋带来的艺术辉煌。皇家画院与诸多皇家艺事,因皇家收藏而留下的国宝级别的文物,尤以宋徽宗赵佶时期绚烂耀眼于世;而他本人的绘画创作以及他以一国之力赞助的艺术家们的绘画创作,是他留下来的一笔带有开创性的人类精神财富。他所留下的一切艺术符号标记了他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以一国之力赞助经营的皇家各种艺苑在实践他的理想中,收藏了人类的精神事业,从世界史来看,他不愧是“美第奇家族”(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事业的先驱。这才是他不死的灵魂,永恒精神的遗产,而赵姓王朝却早已灰飞烟灭。
如果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帝王尺度,如今我们能记住二十五史里的几位帝王呢?这些帝王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可以普世并流传的精神价值的承载体呢?若以文化个体性作为衡量一个个体的尺度,那么宋徽宗赵佶没有让帝王的强势侵占他内在的灵性、剥夺他的文化个体性,而是在帝王与个体之间选择了“个体优先”,并以美超拔了他个体人性的美好一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他也许不能选择历史,但他就是他,他尊重了自己的禀赋,为一个时代赋予了艺术气质。他有这个实力,无论是他本人所禀赋的艺术才气,还是他所能掌控的皇家财力,都足以使他推动和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以一国之力赞助支持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与收藏,历史记住了他,文明记住了他。
当然,还有那岩岩若孤峰的皇家画院所取得的辉煌艺术,也印证了宋徽宗赵佶的光芒。其实,皇家画院早在五代时就开始了,那时的翰林待诏们主要为帝王或贵族画肖像,以及将朝廷的重大活动场景描绘记载下来。随着宋朝历代文治的社会风尚,画院逐渐摆脱聚集画匠的单纯功能,开始追求绘画的本质和艺术的格调,打开心灵和精神的自由之眼,将它们的观感付诸于绘画上。特别是在宋徽宗赵佶、高宗赵构、孝宗赵眘时代,应该是画院最好的时期,尤以徽宗为最,大概是他的艺术天禀,使他不由自主地将生命中最具灵性的智力都倾注到画院和宫廷的各类艺术事业上。

宋徽宗 赵诘 《听琴图》
宋徽宗积极完备皇家画院制度,主要是提升画院的规格,由翰林图画局直接管辖。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他在1104年正式将画学纳入科举考试,考试分六科,如禅道故事、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徽宗亲自出考试题,他常以古人诗句出画稿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格调在“无”字上,“深山藏古寺”,趣味在“藏”字里。时光被藏起来,给自由精神一个绝对静止的自然空间,人性可以纵浪大化之恣肆,但姿态却谦卑含蓄,画面上给出一个几近空无的美学逸趣。如果我们把自由作为一个美学标准的话,“无”也可以是一种姿态,在老庄自然哲学里隐含着一种绝对自由的气质,这正是宋徽宗的艺术品位。考生根据出身,分“士流”与“杂流”,前者有文士背景,后者或为工匠身份。学生除学习绘画外,还必须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种书。“士流”兼选修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同时,宋徽宗设立“书学”科,由翰林书艺局管辖。学习篆、隶、草三书体字,同时修习《说文》、《尔雅》、《论语》、《孟子》,自愿修习大经。宋代的“大经”,指《道德经》、《黄帝内经》、《周易》,“小经”有《孟子》、《庄子》、《列子》,“律学”包括断案和律令,对于画院书院的艺术学子们来说,还是相对轻松的,从科举还以五经四书为必考科目来看,他们的艺术灵感得到了比较好的爱护。
能入画院的画师,俸禄优厚,以翰林、待诏的身份享受与官员相同的待遇,并授予头衔,有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如此完备,可谓中国最早的美术专业学校了。画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以画院为首,其次书院,再次琴院、棋院、玉院的百工等技艺人员皆在下院。支给其他局里的工匠报酬叫“食钱”,而书画两院的报酬叫“俸值”,表明对待艺术家和工匠的不同态度。因艺术的关系,画家还可以获得高官显爵,光禄寺待丞,最高可升至国子监。当时画院更是高手云集,诸如擅画市井百业的张择端,擅画百马、百雁的马贲,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
其实,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就是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寀、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还有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都汇集到宋朝宫庭画院。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三人先后在不同风格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这一时期还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宋室南迁,宋高宗恢复画院,广收流落民间的宋徽宗的字画以及皇家各类收藏,画院的画家能逃脱出来的,皆随衣冠南渡,辗转集结于临安画院,恢复画职,成为南宋继北宋以国家力量进行“文艺复兴”国力主干。
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擅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林椿则以善画花,荣升为南宋画院待诏并蒙赐金帶。著名如马远曾祖、祖父、伯父、父亲马世荣、兄长、儿子马麟一门五代7人相继供职南宋画院,成绩斐然,尤其马远最为著名,有“独步画院”或“院中人独步”的美誉。
宣和四大名著与皇家收藏
宣和是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从公元1119年到1125年,徽宗时代结束。似乎是某种天命的谶味儿在暗示,也许是宋徽宗的学理化素养和职业化严谨的惯性,总之,在这七年里,他开始了对此前所有的艺术活动进行全面有序地梳理和编纂,《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宣和博古图》的完成,是宋代艺术及其收藏的一个高峰展示,从书的编纂体例到收录的作品之精,称之为中国古典艺术之四大名著亦不为过。
谈中国古典艺术,宣和恐怕是最火的年号了。如果说宋代是文艺复兴运动之渊薮,那么宣和那七年间便是这一运动最饱满的结集期。北宋沦陷了,文艺复兴之晚霞在四大艺术名著收尽最后一抹辉煌之际灿烂收官,随着宋人的衣冠南渡,复为南宋文艺复兴之朝霞。
宣和年成为宋徽宗以及皇家艺术的收藏丰收年,除了宋徽宗独创的“宣和体”绘画外,四大艺术名著竖起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标杆,展示着北宋人的精神天际线。它们以凌空之姿,昭示着人的内在追求及其普世的力量,即便是在金人入侵的战乱仓惶中,南宋人尤其是宋高宗,便开始高蹈徽宗铺垫好的艺术轨迹,在文艺复兴的天际线上前仆后继,按四大艺术名著之图,去寻索流落民间的艺术珍品之骥,复兴北宋文艺。
《宣和睿览册》,宋徽宗的花鸟画被称作“宣和体”,它承载的应该是一种艺术的荣耀,这种荣耀并非来自宋徽宗的皇帝身份,而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他对“花鸟”绘画所倾注的心灵“工笔”以及独创的笔墨韵致。但一般评价却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而强调宋徽宗身为帝王对家国的祥瑞期待。这也无可厚非,自然是人类的先生,是人存在的前提,当然也是政治理想的托所。花鸟虽然能愉悦人心,却不一定能愉悦政治,可政治却要主动迎合或取悦人心,当然政治没有那份花鸟的自然闲适和淡定。大概宋徽宗热衷画花临鸟,是潜意识里将两种“取悦”合二为一吧,政治的无为“取悦”是一种为政境界,这和他以道治国是一致的。但“宣和体”的意外收获却是艺术,这一点,宋人邓椿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画继》中写道:“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臻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籞;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橘、骈竹、瓜花、米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记: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茉莉、天竺婆罗,种种异产……赋之咏歌,载之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亦十五种,作册第三。有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
今人在评价宋徽宗的花鸟画或《宣和睿览册》时,大多引用这段话,但就是绕不开徽宗为朝廷祈福祥瑞的政治功利诉求。一是徽宗的身份,再一是他们早已习惯于以政治道德标准绑架艺术,才使他们陷入了艺术视野的盲区、堕入政治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终致于忽略了作者最后一句关于美的“断语”。
这就是《宣和睿览册》的由来,宋徽宗命画院画家将宫苑中异花珍禽一一图绘,凡十五种为一册,共有15000幅图,累至千册煌煌。据说,其中画品之丰富,相当于几十位专职画家一生之作的总和,就宋徽宗个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以一人之力而为之的。“睿览册”取自睿览殿,那是经过宋徽宗钦点定稿的花鸟,才能写为丹青,入之画册。所以,有些画有可能是他和宫廷画家商议定稿,或指定代笔,或由他指点作画,这一类为宋徽宗的代笔画数量不在少数。这些画多是细笔写实一类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画科,据目前研究所能得知的代笔画家有刘益、富燮。还应该有更多的专事“供御画”的宫廷画家,据说,在北宋后期的花鸟画上,很少看到画家的名字,有可能是终身代笔者的奉献。他们的代笔画被称为“供御画”,这类画,宋徽宗在上面题诗或押署并钤印,基本为“御题画”。但是,这些代笔者的艺术成就不可忽视,他们的工笔之精细,姿态之生动,非专门写生而不能为也,再加上诗、书、文称配,令人叹为观止。
《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完成《宣和睿览集》后,徽宗又开始着手“二谱”的编纂工作。据说,“二谱”是由宋徽宗亲自编著,也有认为是蔡京、米芾所编。米芾被召为书画学博士,从内容看,全书贯注了宋徽宗的编辑理念,应该是宋徽宗倡导的文艺复兴的艺术工程之一。宋初,就开始了古书画的搜访和积累工作,到徽宗时,内府收藏非常丰富。据俞剑华先生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精装本《中国绘画史》中有评价,他说:“万岁之暇,惟好图画。内府所藏,百倍先朝。”再加上当朝画院画家们的当代作品,激发了宋徽宗梳理绘画史的灵感,于是在他组织下,将宫廷所藏魏晋以来的历代绘画作品6396件,画家231人,按题材分为10个门类进行编辑。其中,道释49人,人物33人,宫室4人,番族5人,龙鱼8人,山水41人,畜兽27人,花鸟46人,墨竹12人,蔬果6人。
编著画集的体例,按照门类,每门先作叙论,叙述画科起源、发展以及代表人物,其次,按时代先后排列画家小传,包括籍贯、仕履、才具、学养、擅长、故实等,传后再具列作品目录,完成了《宣和画谱》共20卷这部巨著。这本书不仅仅是宋代宫廷收藏的一部绘画作品编目,还是一部记传体的绘画通史。
像顾恺之、展子虔、阎立本、李煜、僧贯休、武宗元、周昉、顾闳中、李公麟、李赞华、王维、关仝、李公年、王诜、范宽、董源、童贯、韩幹、黄筌等等皆因这本书而流传下来,使得这些构成中国独有的艺术风景的艺术家们才有机会恩泽后人。
画院里的画家们的作品,也享受了与各时代作品相同的待遇,被皇家收藏并被编入“二谱”。《宣和博古图》,这是一部皇家收藏图录,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包括一些著名的重器,是宋代金石学重镇。宋徽宗敕撰,王黼或王楚编纂,30卷。大观初年(1107)开始编纂,直到宣和五年(1123)才成书于宣和殿。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从殷商到唐代的青铜器20个种类,839 件。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每一类有总论,每一器都摹绘图象,勾勒铭文,或注铭文拓本及释文,记录器皿尺寸、容量、重量等,间附出土地点、颜色和藏家姓名,对器名、铭文也有详尽的说明与精审的考证。每一图旁标注器名,器名下注有“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说明图象之比例。
宋人还根据这批国家收藏的青铜器实物形制,订正《三礼图》得失,为宋代国家大典制作礼器提供依据,规定名称,如鼎、尊、罍、爵等,一直沿用至今。《四库全书总目》评述《宣和博古图》所录铜器,形模未失,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据王国维先生考证,书中所录的铜器,在“靖康之乱”时被金人辇载北上,而其中的十分之一、二,曾流散江南。国之重器,不可以假(借)人。高宗时不惜花重金搜寻散失的青铜器。
郑欣淼先生在专著《天府永藏》中,谈到了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时特别提道:“中国历代宫廷都收藏许多珍贵文物,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
当然,宫廷收藏远不止这些,诸如徽宗所藏端砚,就有3000余方,著名墨工张滋制作的墨块,竟超过10万斤,而点缀在艮岳上的珠宝珍彝、奇花异石,不可胜记。但都不及宣和四大艺术名著,这四大名著因集中展示了宋代文艺复兴的文化样式而不朽。
赵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还处于知识素材阶段的艺术样品和藏品进行了纯粹的学术整理,并建构了新的知识体系。更何况他并没有以皇权挟带意识形态的私货,干扰艺术的纯粹性,相反,他对艺术的纯粹趣味的忘我投入和终级追求,保证了整个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纯粹性。
艺术与王朝
艺术不是王朝国家的目的,与王朝国家的本质亦相背离。一个王朝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经营财与兵,王安石新政以后,解决了财与兵的问题,王朝有钱了,可以为艺术而工作,加上辽金谈判换取了和平的结果,不打仗了,也正是可以转型为艺术而工作的时候。不养兵,那就多养艺术家吧。
艺术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品,一个能为艺术而工作的王朝国家,除了财力有余之外,还要有一种爱的热情。艺术是一种传递爱的行为,是一种爱“爱”的方式,爱自然,爱生活,爱人类,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作为王朝国家,宋代300多年的王室留下了一个热爱艺术并以收藏艺术为王朝义务的传统。
这种有着“文艺复兴意味”的皇家收藏,与当下的金融资本参与炒作下的泡沫收藏截然不同。宋王朝作为政治实体,不仅参与经济,还参与到艺术工作中来,以一国之力,赞助和参与创造人类的精神财富,它有着一种自觉创造历史的使命感,是一个国家开始对于文化、对于精神消费需求的自觉。在历史上,从另一方面说,能够留下光彩一笔的王朝,有幸能够进入人类精神史的国家,也是荣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