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同吾
张同吾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多年在高校中文系执教,1983年调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专事诗歌创作的宏观研究和诗歌评论,主要著作有诗评诗论集《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意象和雨的精魂》《青铜与星光的守望》以及小说集《听海》,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随笔集《放牧灵魂》等,多次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一
1947年6月,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全家登上从滦县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叫北平,国民党迁都南京便改称北平了),虽然内心很激动很快活,但或多或少也有些惆怅。火车的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轰响,窗外的树木向后奔跑,故乡渐行渐远了,童年的伙伴和故土风情,也许今生难再重逢。曹操说曹植是“生于乱,长于军”,我是生时“国破山河在”,长时“恨别鸟惊心”。少不省事,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是隐约有点惆怅。
我们全家到北京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前门车站灯火辉煌,走出车站看到穿着蓝色坎肩印着号码的三轮车夫们蜂拥而上抢着拉座,也掺杂妖艳的女郎搔首弄姿,远处是有轨电车叮当叮当地在大街上行驶,电线上时时闪着幽蓝的光,呈现出一派大都市的繁华。其实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虽然战争越来越近了,时局越来越动荡,北京的民众生活依然保存着古老的风情,过着平静的日子。北京没有高楼大厦,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闭门而居,胡同里人迹稀疏,几乎没有车辆。偶见两个旗人相遇,男的作楫,女的打千儿,就是双手上下相握放在腰的右侧,双腿做下蹲状,相互问候,您家老爷好?太太好?少爷好?小姐好?客套琐繁之至。即使是穷旗人也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儿子为少爷:“您家少爷干什么营生呢?”“蹬三轮儿呢!”当年深宅大院有自来水,小门小户备有水缸,都靠买水,街上有水房,笨重的木制独轮车两边各有一个长方形大木桶,四角是圆的,给小户人家送水,嗞嗞扭扭的声音,就让小胡同里更显得幽静。家家生煤球炉做饭,每晚熄灭每天重新生火,下层劳动者均无隔夜粮,贫穷使然也是习俗使然,每临中午女人们把废纸点燃扔进小小灶堂,再扔进几根劈柴,用铸铁的或铁皮的小烟筒把火拨旺,再放进煤球,于是家家户户就烟气腾腾。这时老爷爷或老奶奶或媳妇们从街上买回二斤棒子面蒸窝头,也偶然买二斤白面烙饼。他们烙饼是用一种砂锅,上面有许多圆孔,反扣在炉子上,上面也不抹油,干烙,我相信一定不好吃。家家连煤球、劈柴也是现用现买。老北京们即使是汉族,也延续了旗人的讲究,几碟咸菜也切得极细致,放上点佐料,吃起来有滋有味。住在大杂院里那些蹬三轮的、拉洋车的、当工匠的、出小摊儿的、练把势的、算卦的劳累一天回到家中,买上二两猪头肉或羊杂碎,喝上二两高梁烧,也很自在!各家过着相同的日子各不相扰,却又客客气气亲亲热热,这在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
我们来到北京先投奔一位朋友家,不久在阜成门内的福绥境胡同租了三间南房,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中等四合院。这条胡同是南北走向,这所院落在胡同北口路西,前院有几间北房,南墙下种植花草,房东住里院北房三间和两间耳房,正房前搭着高大的凉棚与房檐相接,院中有一个大鱼缸养着金鱼,这是北京有钱人的标志:“凉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先生”是指管账的,丫头即指使女、丫环,这家是否有石榴树已不记得,反正没有“先生肥狗胖丫头”。房东是这家男主人,四十八、九岁与我父亲年龄相似,白白胖胖,既不做官也不经商在家赋闲。自民国初年始,三十余年间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人,或清代遗老遗少,或官僚后人,靠祖辈或父辈留下的遗产积蓄过活,不很富贵却衣食无虞。他有一儿两女,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女儿们比我姐姐稍长。晚上他经常携妇将雏去听戏(北京人看京戏叫听戏),有时也在家中伴着留声机清唱。他们都睡得很晚,日上三杆才起床,在院子里刷牙漱口,弄得牙刷牙缸哗啦哗啦地响。我们与他家只是房东房客关系素不往来,大约也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很难融入北京传统的生活习俗。这类人家属于中产有闲阶层,没有私家包月(包租的三轮车),出门顾三轮或洋车(祥子拉的那种两轮人力车)。胡同里人稀疏,需走到大街上才能顾到车。真正的富贵人家,像鲁迅说的,不是什么金呀玉呀,而是“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真有点《红楼梦》中的景像了。
我家四口人住在三间南房,门前有三层台阶,室内两明一暗很宽敞,很新的木板地和雕花隔断。那时学校即将放暑假,不便办理入学手续,我时时随父亲闲逛。有时全家去北海公园,那时公园内幽静极了,人迹稀疏只有花香鸟鸣,偶有一两人在五龙亭垂钓,偶见一两对情侣在树荫下相依,或有三五只小船在水上飘荡。我也同父亲去过景山和故宫,那时崇祯皇帝上吊的枯树还在,父亲久久地站在那里凝视,向我讲述李闯王的故事感叹历史兴亡。那年我才八岁,自然不懂其中血泪,但似乎朦胧感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贼尚能苟活,而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那时故宫中的解说员大多是太监,他们没有胡须,说话都女声女气的,走起路来还略微一扭一扭的,我感到很奇怪。我问父亲,他们是男是女?父亲说是男的,从小把小鸡巴割掉了,就成了半男半女的。“他们怎么洒尿呀?”“蹲着。”“为什么要把小鸡割掉呀?多疼呀!”我长大以后逐渐明白,中国自古就是“有特色”的。不仅有四大发明,而且在宫闱之中把男性文化发展到极至。这些太监们在清朝灭亡时20岁左右,有的才十几岁,是清末宫廷生活的亲历者,也是政治风云的见证者。此时他们50岁上下,个个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寻,只能在这里终老。一位太监向我们讲解许多宫中轶闻轶事,我只是东张西望,完全未听他之所云,只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在后花园中有一个院落,正厅屋脊四面有四条龙,院中有一个硕大的鱼缸,他指着其中一条龙说,他亲眼看见每天深夜它都到这个鱼缸来喝水。这令我毛骨悚然。我想,故宫有九千九百九十间半房(也许是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古代又没电灯,每到深夜烛光悠悠,这里是多么阴森。他还讲了刘罗锅与何珅斗智斗法的趣闻,后经父亲的多次重述,我从中感受到盛世皇帝的闲情逸致与末代皇帝惶恐不安相对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父亲喜欢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那时在西单商场二层楼上有一个游乐茶座,大约每晚或隔一晚他俩就来这里表演。场子不大,似只能容纳六七十人,前两排是沙发,罩着白色布罩,前面有茶几,可放茶水和小吃,后面则是木制桌椅。当时侯宝林、郭启儒已是名星大婉乘坐包月车赶场,有时先在东安市场吉祥剧院表演,然后风尘扑扑赶到西单。我父亲有几次带我来这里听相声,说的什么段子我完全忘却,只记得坐在这里有一种安闲之感。坐沙发和坐木椅,票价悬殊,通常我们都坐木椅,散场时我在沙发间有些留连,看到这神态,父亲报之微微一笑,后来也曾买过沙发票,满足我的虚荣心。
我家离白塔寺近在咫尺,父亲常带我去看庙会,几层院落之内热闹非凡,卖油茶的、卖馅饼的、卖糖果的、卖玩具的、卖大力丸的、卖锅碗瓢盆的、卖各种衣物的小摊贩高声叫卖,游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最爱看练杂技,顶缸的、顶幡的、摔跤的、练车技的,都那么彪悍、勇敢、灵巧,我看得十分入神。每表演一轮就要收钱了,一个光膀子的壮汉,手持托盘围着场子转,嘴里喊着:“各位老少爷们儿,有钱的请您帮衬,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时有人离开,他便放声开骂:“您忙什么呀?回家报丧去呀!”“您急什么呀,天还早呐,就想上床×媳妇呀!”围观者哄然大笑。这是一种京腔京调的粗野,我长大成人之后回忆起来,这种语言模式离庙堂文化很远,离深深的庭院很远,这种软性的粗野,是皇城脚下独有的另一类市井文化。
在庙会里我也喜欢看玩具,各种款型的小汽车和小汽艇小轮船,都让我蹲在那里留连忘返。父亲对我宠爱有加,有时他温和地问我:“买一个吧?”我说:“不,看看就行了。”我是个早谙世事的孩子,也是很孝顺的孩子,我知道家境已衰,花钱要节省,不可随心所欲了。有一次父亲坚意为我买了一只小汽艇,是铁皮的,船仓内有一个小碗儿,放入煤油,有一个棉线拧成的捻儿在小碗内,点燃之后靠蒸气摧动汽艇前进。我把一个大铁盆放满水,小汽艇就在水上游弋,我一玩就是半天。这时我的心境是安实而温馨,我在这种安实而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2007年张同吾主持第二届中韩诗人大会开幕式
二
我们在福绥境住了半年,于1947年冬天,父亲在西四北小糖房胡同买了一座小四合院,有北房三间,东房一间是厨房,西房半间是厕所,另半间是储藏室,南房是两间半住房,半间门房,北房三间是花砖地面,玻璃门窗阳光明亮。西四是北京的繁华地段,在十字路口因有四座石碑楼而得名,全称是西四牌楼,与东城的东四牌楼相对应。牌楼有三个门,中间走汽车和对开的有轨电车,两侧走自行车,造型壮观雕刻精美,是十分有品位的古典建筑。到了1950年代中期一纸“御批”全部拆除,相继到了1958年“大跃进”,就连东直门、西直门、阜成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及外城的几座城门都统统拆除了,只保留了德胜门的箭楼,梁思成等大建筑家们,再三请求要保护文化遗产,毫无作用,他们为之痛心疾首痛哭流涕,伟大领袖说: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是很成问题吗?日本鬼子进北京他们不哭,拆了几座门就如丧考妣!这是后话暂可不提。
小糖房胡同是西四北路东的第一条小胡同,胡同口就是有轨电车站,商店、邮局、鱼店、同和居饭店都集中在这里,这条小胡同仅十几户人家,我家在最东头,离胡同西口不足百米,是闹中取静。买这个院落花了多少“金圆卷”我不知道,后来父亲说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下出售绝不少于千万!
在这个宁静的小院子里,我可以尽情地玩耍,西邻有一面很高的红砖墙,紧靠我家西厢房,又高出一米多,我放学后就在那里玩皮球,把球向红砖墙上投掷,弹回接住又投掷,反反复复,乐此不疲。后来我在院门内的东墙上安装了一个小篮球筐,买了一个大皮球,权当篮球(我八、九岁时打不动篮球,后来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去天津看望暂居那里的父亲,他才给我买了一只篮球),我在那里定点投篮,也做三步上篮,这些童年的玩耍,对于后来我打校队右前锋,成为得分手也许不无关系。我自幼好动,每有客人来常常把自行车停靠在正屋窗下,又每逢假日我不上学,就推着他的车在小院子里转圈,然后就试着骑,个子小无法迈上车座,就从车梁下蹬着骑,先是蹬半轮,后来就能圆熟自如,在小院里旋转就像马戏团一样。就这样我在小学二年级无人教,便会骑自行车了,我家有一辆德国黑人牌大二八自行车,爸妈怕我骑车危险,先是锁着不让我骑,经我多方央求,就推出院里在东面宽敞的大拐捧胡同骑。有一次正恰遇一个老奶奶提两桶水放在地上,老奶奶在一旁稍做休息,我骑车围着水桶兜圈儿,一不小心把一桶水碰翻了,老奶奶大骂,我仓皇逃窜。长大后想起来真对不起这位老人,她提两桶水多艰难啊!
过春节是十分快活的日子,在白塔寺附近的北沟沿有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临近春节了父亲就带我到那里去买爆竹、二踢脚、响鞭和各种烟花,满载而归,我就在院里独自燃放。没有观众,父母也不看,当然在除夕之夜,姐姐也来凑凑热闹,过一会儿她就回屋了,我独享其乐。过春节,父亲会给比他年长的几个老朋友拜年,一般不带我去,因为带上我等于向人家去索压岁钱,而平时他是很愿带我去朋友家的。每年父母给我一块钱压岁,亲友来拜年有给一块的,有给五毛的,在当时也不算少了,当年一块钱和一块银元相等,这种比价延续好多年。给我压岁钱最多的是刘介臣伯伯,他每年都给我十块银元,相当于如今的近万元人民币。他原是哈尔滨最大的资本家,他比我父亲年长约20岁,高高的个子,丹凤眼一缕灰白长髯,貌似关公,他可能是排行老三,在哈尔滨时人们统称他“刘三爷”,去拜会他也称三爷,我父亲叫他三哥,在旧社会如果单单有钱,是不敢称“爷”的,哪怕家财万贯也不能称“爷”,“爷”不是他自己封的,是社会上人们的共识,只对既有钱又有威,白道黑道都通达的人才被称“爷”,这种人上交官府下交匪,且又为人仗义主持公道,如果有哪位商家被土匪绑票了,或吃官司了,刘介臣派人出面,立即放人。他绝不像我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那些黑社会“老大”,一身匪气霸气,后面还跟着几个戴墨镜,穿灯笼裤的打手,那是一些下流混子。而威震一方的阔佬 ,却像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文质彬彬的,我父亲说别看他如此和霭,当年也是一跺脚地抖三抖的人物。每年我父亲初三或初四去给他拜年,他在正月十五之前也回拜,有时带他的小夫人前来。大夫人是结发之妻,与他同庚。小夫人才40岁左右,长得很漂亮,曾是哈尔滨的名妓,我父母称她三嫂,尽管我父母比她年岁大得多。每次她来都坐在里屋与我妈妈聊天。我母亲对娼妓自然心存鄙视,她同其他朋友的妻子闲叙时,议论说妓女毕竟也是风尘女子,那种笑容与良家女子的确不同。母亲是极聪颖的人,通达事理人情,她对这位“三嫂”亲热而尊重。我也曾随父亲到过刘伯伯家中,他迁北京后已失却昔日繁华,但俗话说:“船破有底,底破有邦,都破了还有一堆大铁钉。”他住一个很大的庭院,正房五间花砖铺地,客厅两侧是雕花木隔断,两个夫人匆匆相见就退去,有佣人上茶,我坐在一旁吃点心,听父亲和刘伯伯闲叙。刘伯伯对我很亲切和蔼,然而从他器宇轩昂中依然想到他当年的八面威风。记得他还赠我父亲两幅齐白石的画,所憾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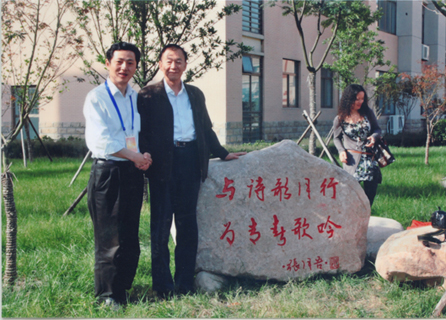
2009年第二届徐志摩诗歌节在海宁举行,为之题词刻碑
三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林彪罗荣桓领导的第四野战军入关,到了1948年平津战役进入紧张鏖战状态,电视连续剧《北平战与和》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态势,细致地描绘了傅作义的心理图像,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十字路口,正面对命运的抉择,这种抉择也决定北平是毁于战火还是和平解放。这是世人难知的困难险境,后退无路前行无门,蒋介石对他恩威并施,步步紧逼让他率部南归,做为非嫡系将领率残兵败将到了那里是何处境?如果投奔共产党又是前途未卜,何况又有特务盯哨军警密防,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有太多的焦灼、犹豫、无奈和痛苦,面对王朝末日、大厦即倾,独木难撑。
面对这种局势,北京各阶层的人们是怎样的心理形态,我是小孩子难以窥探。一位叫田纯仁的伯伯常来我家与父亲闲谈,一聊就多半天。他是位懂政治有见解的绅士,是我父亲在哈尔滨天丰东当副总经理时董事长田熙久的二弟,父亲称他二哥。因为其兄有钱,他一生都不工作,在家中读书看报清谈,他住乐亭时,国民党陈昌捷上将专程到他家拜访。此公博学强记口才又好,总是听他讲,父亲默默地听。我能听到只言片语,他们主要谈论时局,感叹国民党的昏溃无能。似乎也谈及是否搬迁至台湾或香港,田伯伯的妻子是张厉生的亲妹妹,张厉生早年留法,抗战时在武汉相当活跃。郭沫若的《洪波曲》对他也多有描述,1948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当时通货膨胀,蒋介石委派宋子文、孔祥熙和张厉生分赴东南、西南和华北推行由“国币”改“金元券”。张厉生来到北平在故宫太和殿前讲演,电台予以直播,是一口纯正的乐亭腔。那天田伯伯又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厉生来北平了,晚上在鸿宾楼请你吃饭,大哥(指田熙久)也去。张厉生请我父亲,不仅因为父亲与田家交厚,当年田家企业兴衰系他一身,而且父亲与张厉生又是昔日同窗。但父亲还是婉拒了这次邀宴,只说请代问候就是了。当我成年之后与父亲谈及此事,问他为什么拒不赴宴,他说虽是同学,但人家是高官咱是百姓,不必攀龙附凤。父亲的平实、恬淡、谦和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性格和人生观念,自幼年就给我深深的熏陶,直至从深层影响到我的文化性格。我在中国作协工作17年中,对各届领导都很尊重,但从未登门拜访,除非他们找我谈工作,逢年过节也不曾打电话拜年,我并非恬淡到迂腐的程度,也并非是狂傲,而是深恐有“拍马”奉承之嫌,我有许多高官巨贾朋友,那是无功利所系,心曲相通、相互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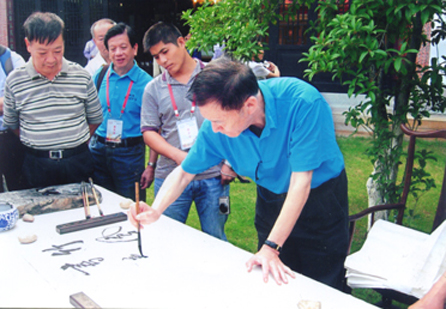
2011年在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诗人节为之题词
动荡的年代,生活的表象依然平静,每天早晨去上学,天暖放晴的日子,我就推一支铁环上学,一般的铁环是铁条做的,显得轻飘,我的铁环是父亲到铁匠铺请人用铸铁定做的,直径大约2尺,配制一根铁棍,顶端是M型,手把是木制的用它推着铁环穿街过巷直奔学校,就连上台阶都不倒,有时在西四南花一毛钱吃十个锅贴,又推着铁环上学了。在小糖房胡同东口与我家一门之隔就是胜利电影院,不知什么时候我交上一个大朋友,他在电影院工作,二十七八岁,穿戴整洁,文质彬彬既不是经理又不是检票售票的,他常送我进影院看电影,不必买票。既看美国侦探片,也看中国故事片,当时轰动一时的就是《第十三号凶宅》,据说实有其事,那“凶宅”就在北平,看后挺恐怖,然后还想重看。也就在那时候,记住了赵丹、白杨、王丹凤、李丽华这些明星,特别是尹秀岑和韩兰根,尹是大胖子,韩是小瘦子,二人在一起演喜剧,总是逗人捧腹大笑。我已不记得这位大朋友的姓名,他还带我游北海,还在照像馆照过一张合影,也到我家来找过我。我迄今不能理解,他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结交我这个不足九岁的孩子,而当时我的父母也竟然丝毫没有戒心,大约那时候人心尚古吧。还有一种解释,我自幼人缘好。
父亲也曾带我去过中南海,这时中南海已不是公园,而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所在地,它与南海相隔,市长何思源在中海办公。父亲与何并不相识,同他的秘书是同乡,承他相邀到那里作客。何思源的会客厅很朴素,只有几对沙发,墙上好像也没有蒋介石的肖像。这位秘书的姓名我已忘却,他偶尔到我家去,有时也留下吃顿便饭。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我母亲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就在我家相识,待女方告辞后,我妈妈批评他:“你第一次同女孩子见面怎么穿这么旧的西装啊?一点都不注意仪表!”他说:“大婶,我不怕您笑话,我只有这么一套西服。”堂堂北平市长秘书,只有一套旧西装。还有一件事是北平解放后,他觉得以他的政治身份不便留下,要飞香港再去台湾。他没有钱买机票就到我家来借钱,姑且不说这种“借”何日还,我也不晓得是否“借”给了他,待我成年之后经常想起这两件事,确信他的确清廉。国民党军政官员中,有多少人恶贯满盈腰缠万贯,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五子登科》,生动地描绘出那些“接收大员”,对房子、金子、票子、车子、女子的贪婪。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终老台湾连丧葬费都没有,清贫者又何止于右任一人?我曾问过父亲张厉生是怎样一个人,他说为人谦诚忠厚,勤勉认真,为官清廉,为子孝顺。我们年轻时认定,一切反动派都是坏蛋,没有一个是好人,您怎么能夸他呢?近读杨帆著《去台高官》一书,其中介绍张厉生生平和事迹,说了一生积极反共,先入CC 派,后投靠陈诚,深得蒋介石信任,曾任国民党中委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高职,书中介绍他“秉性诚朴、不尚浮华,又为人谦恭,勤奋敬业”,又说他“低调做人、严于自律、好学慎行、淡泊名利”,“既没有置下什么家产,也无什么积蓄,以致退休之后生活十分清苦,晚景凄凉。”书中介绍了为一世清廉,治病付不起医药费,因此看来政治观念、政治道路与个人品质并无关系,而我们却长久地混为一谈。
到了1948年后半年,就打破了街市的平静,我曾看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的学生们高举校旗,打着“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的横幅游行,他们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军警们似乎已顾不上阻截,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经势不可挡。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破败景像在街头随处可见,在宣武门内、东安市场、西四南大街处处都有旧货市场,明代清代瓷器琳琅满目,还有许多更早年代的古玩,也有许多红木的、紫檀的桌椅条案,其价钱之便宜,现代人难以置信,三两块钱就能买一只青花瓷的盘子或一只碗,十几块钱就能买一套红木桌椅,有的太师椅的靠背还镶着汉白玉面,上有自然的山水画。都在卖却少有人买,那时人的心态是共产党要进城了,谁还充当有钱人?那时没有膺品,真的器具和古玩尚且如此便宜,谁去仿制呢!
1948年9月我升入三年级,到了11月,空气越发紧张,解放军开始围城,千年古都会不会毁于战火?我家房顶会不会落下炸弹?几乎人人恐慌。姐姐帮助妈妈一起在窗玻璃门玻璃上贴上米字形纸条儿,避免玻璃被炸弹震碎而伤人。惟恐断粮断水,父亲住家中扛回大米白面,买了水缸储存满缸的水。家家如此,一副备战景像。这时北京周边的县城密云、顺义、平谷、房山、昌平、通州就连与市区近在咫尺的清华园、燕京大学都被解放军占领了。西郊机场、南苑机场都被解放军占领,就在东单广场,也就是同仁医院以北的那块地方修了临时机场,达官们从这里飞往南方,蒋纬国秉承父命来游说傅作义,也在这里起落。傅作义守军在景山上安装了巨大的警报器,不知是试验还是真的有什么“敌情”,真的拉响了警报全城都能听到。北京内城是南北十里,东西十里方方正正,从东西方向丈量,朝阳门离东四2.5里,东四至西四5里,西四离阜成门2.5里,盛新小学在西四以东景山以西,警报声听得更真切、声音由小至大,由缓至急尖厉刺耳,我们把课本铅笔盒胡乱往书包里一塞,就蹿出教室往家中奔跑,街上车拥人挤,有的铅笔盒从书包中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拣,那种慌乱可见一斑了。后来傅作义的军队都撤退到城内,连盛新小学也驻满了大兵,我们就停学都回家了。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初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一队进永定门、前门,林彪、罗荣桓就站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一队进入西直门,经新街口至西四大街南行,大街两侧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拥挤得水泄不通。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我和其他孩子们都戴着棉帽子和棉手套,捂着耳朵挤在群众之中,看到一队队战士雄壮威武,一辆辆坦克车、装甲车、大卡车上都站着穿棉军装戴毛绒绒大皮帽子的战士们,挥手向市民们致敬。北平免于战火获得新生,让所有有良知的人感到庆幸。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首先让年轻人感到兴奋和喜悦,温济伍伯伯的外甥赵树新,那时正在北京40中读高中一年级,温伯伯与我父亲常有信息相通,就委派他骑一辆自行车来到我家,那时我和姐姐叫他哥哥,后来成了我的姐夫。他向父亲说完事情,就教我和姐姐唱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南泥湾》,在歌声里,我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这大约就是时代的青春气息在年轻人心中的投影。
盛新小学的老师们从总体来看,与其他学校的教师相比,思想会滞后一些,但他们之间也会有种种差异,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中,他们也会不断进步。当时学校领导不管内心怎样想的都要按上级要求办事,10月1日那天在校门挂起红布大横幅贴上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标语。学校组成了秧歌队,有位老师专门教几个学生打腰鼓和打镲,二十几个高年级学生跟着鼓点儿在校园里扭秧歌。今天想起来,那些小男孩儿抡着双臂扭着屁股,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我对他们羡慕极了,我真想跟着他们去扭。可是人家都是从五六年级挑选的像模像样的,不要四年级的,可我特想加入其中,于是千方百计说服了秧歌队长,我终于加入秧歌队真是喜出望外。我们不仅在校园里扭,还走上街头,从西四到平安里到地安门向南到故宫后门再返回学校,扭这么一圈儿有十几里地,得耗多大体力啊,而我却十分快活,特别是观众越多扭得越起劲。我这一生不求物质,只求精神,只求别人赏识,是否从那时已露端倪?
开国大典在下午三点举行,我们小孩子不能参加,在街上看到人们个个脸上都挂着无法按捺的笑容,高举新缝制的五星红旗,高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涌向天安门广场。大街小巷一片欢腾,伟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啊,多好的比喻,原来睡着、跪着、趴着,现在自立了,谁不兴奋呢?至于“站起来”以后做什么,是走向富裕还是继续贫穷、是继续斗争,还是和谐安康,那时的人们似乎未去思考。不管怎样,这是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容和历史的走向。——《中外名流》第7期评说·自传










